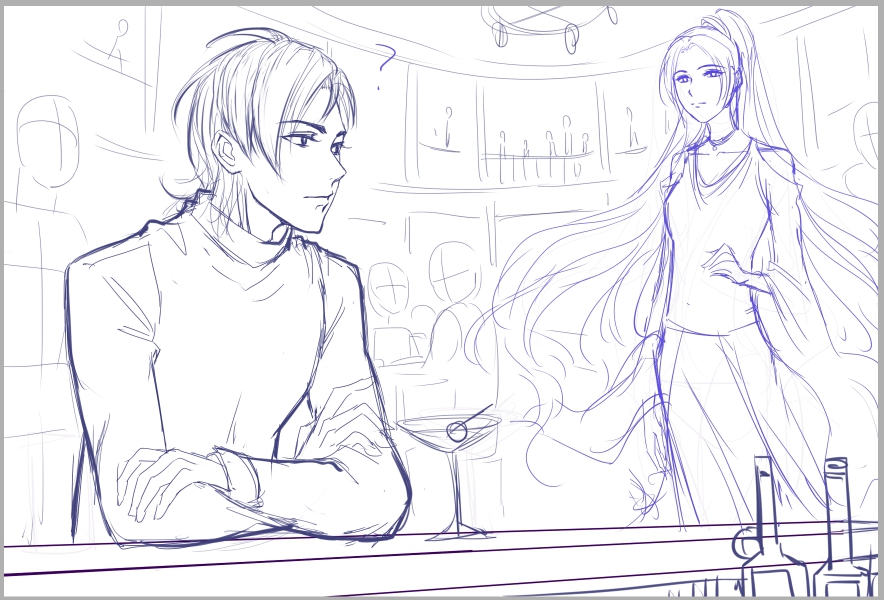第四章《報喪女妖》
本章節 7759 字
更新於: 2018-07-14
隨文附上燈貓百白與蓮華所畫的佩蒂。
我端著酒杯,和桃樂絲與希沃茲窩在角落,觀看來來往往的怪物們。
這是一間位於偏僻處的小酒吧,外頭沒有任何的招牌告示,如果不是熟客,壓根不會想到,這個外表看似破爛,連流浪漢都不屑一顧的建築裡頭,居然藏著一間坐地明顯和外在不符,以現代建築法,絕對屬於違法擴建的古老酒館。
我第一次推開那扇門時,一度以為自己看錯了,於是我又退門口,看了看建築外部,接著才走回裡面,接受這個由怪物經營的酒館。
能把礦山大的酒館塞進不過一個房間大小的建築物裡,還沒有任何人類發現,這只能是怪物的傑作,我還來不及讚嘆這空間魔法運用的精妙,站在吧台的半人馬已走到我面前,塞了張名片給我。「新來的,享有七折優待唷!」
後來,我跟身為酒館主人的半人馬混熟後,曾感慨的表示,空間魔法真是方便,我也好想找個擅長使用空間魔法的傢伙,幫我改造一下我的住宅。
正在替我倒酒的半人馬,半是不解,半是鄙夷的看了我一眼,「空間魔法是給我們這種買不起房子的低產階級用的,你這個有房有車的怪物界勝利組,要空間魔法做什麼?」
說的好有道理,我居然無法反駁。
我端著酒杯看著酒館中來來往往的怪物們,興許是平日扮演人類實在累得夠嗆,這間酒館裡,有的只有全然的怪物,對,就是那種毫不掩飾,該纏著繃帶就纏著繃帶,該渾身毛皮就渾身毛皮,怎麼隨意怎麼來的怪物們。
堅守人類世界守則,堅持扮作人類的怪物,在這只會被罵作是衣冠禽獸。
如果以人類的角度來看怪物間的情誼,大概會是薄情炎涼,諸如此類的評價。
我們不太可能因為一時想念,就繞過半個地球去探望對方,雖然會這麼做的怪物,本質上還是存在的,但是終究是少部份,畢竟,我們的壽命與時間和人類不同。
幾十年,對人類來說,興許是一輩子的時光,對我們而言,不過是頓下午茶,甚至是眨眼間的事,話雖如此,偶爾我們還是會在這間酒吧碰頭。
畢竟有些事,不是知根知底的人,實在難以理解。
活了幾百年的傢伙,一天起床,突然覺得生活枯燥乏味,想找個人發發牢騷,或是那天心情不好,想把什麼人的骨頭給拆下來,再重新組裝,最好不用負起任何法律責任,怪物是你最好的選擇。
有個不知死活的傢伙,跑去詢問前面那桌的棕精靈,最近怎麼沒見他們潛入別人家裡,幫忙人類作家事?
早已喝得滿臉通紅的棕精靈,當下就砸了酒杯、掀翻桌子,揪著對方一頓狂打。「現代人家裡都有掃地機器人,還要我們做什麼!」
又是一個因為科技發達而失業的不幸故事。
棕精靈和人幹架的場面不常見,整個酒館的人都興味勃勃的看著他們揪著對方衣領,又是揮拳,又是頭鎚,身為酒館主人的半人馬,甚至抓準商機,當下就開了賭局。
我看了下賠率,思考是否該去玩一把?
叮嚀。
安裝在門扉上的風鈴發出清脆聲響,吸引了部份人的注意。
一開始是率先注意到新訪客的人,接著,察覺到這份異常的人好奇的往入口一看,接著,原本喧嘩的酒館,瞬間靜了下來。
就連打到眼紅的棕精靈也停下動作,眼也不瞬的盯著女妖。
女妖穿著一襲雪白長裙,那襲衣袍,與其說是紗,更像白霧,又像是暮夜月光,在空中輕輕飄蕩。
就是這麼一位女妖,對整個酒館施加了一項名為沉默的魔法。
每個人都靜靜的望著她。
女妖在怪物界極其有名。
如果要用人類來舉例,她大概就像是埃及的克麗奧佩脫拉,中國的蘇妲己,或是近代的奧黛麗赫本與瑪莉蓮夢露。
她甚至是我所見過的女妖中,最美的一位。
不單是我,在場所有怪物都如此認同,如果換作平常時候,不管是人類,還是怪物,都很樂意請她喝上一杯,但是,今天,沒有人上前向她搭訕。
曾經有人問我,覺得哪個怪物最讓人類討厭?
我沒法回答這問題,畢竟人類的喜好太難理解,哪怕是最可愛的怪物,人類中也有人會對其抱持強烈的痛恨感,但是,如果將問題改成,怪物界中,最讓怪物排斥的怪物是誰?我相信,這個答案只會是佩蒂。
佩蒂雖然是公認的第一美女,個性也相當溫和好相處,但,她穿上那襲長袍時,沒有任何一個怪物會想見到她。
因為佩蒂是個報喪女妖。
一個專門帶來壞消息的報喪女妖,最糟的是,佩蒂帶來的,不只是訃聞,有時她會帶來一些令怪物們的生活產生劇烈改變的消息。
準確度還是令人髮指的百分百。
因為佩蒂的登門造訪而改變一生的怪物難以算清,要命的是,不管對方躲在哪裡,只要還有一口氣在,哪怕躲在荒涼無人的深山叢林,或是深埋地底數丈,佩蒂總能找到他們。
比人類的尋人節目還高效率。
許久以前,曾經有人不知死活的對佩蒂開玩笑,讓她去當個尋人偵探,絕對賺錢,結果,佩蒂揚起一抹有些為難的淺淡笑容,「嗯,我想你們對我有點誤會,我只能找到必須通報消息的對象。」
佩蒂那時說的雲淡風輕,聽的人卻是頭皮發麻。
話題扯遠了。
此刻將報喪女妖那身行頭穿在身上的佩蒂,目光在酒館裡來回巡視,就是這麼一個簡單的動作,讓酒館內本就沉默的氣氛更加壓抑。
誰是這回的倒楣鬼?
我腦裡剛浮現這個疑問,佩蒂的目光已落在我們這桌。
幾乎是在那一瞬間,在我們前頭的怪物們,不管是站或坐,全部跑得老遠,畫面之壯觀,不亞於摩西分海,雖然,我根本沒見過一個叫摩西的人類,也不曾看過他怎麼劈開紅海,劃出一條道路。
最混帳的是,他們撤開時,順道將阻隔在佩蒂和我們之間的桌椅都一塊搬走了。
這也讓道的太過份了點。
我還來不及說些什麼,便清楚感覺到希沃茲全身的肌肉都繃緊了,就連桃樂絲也死死捏著酒杯,報喪女妖的威力,連向來無所畏懼的桃樂絲也不敢忽視。
許久以前,佩蒂曾以報喪女妖的身份找上他們兩人,希沃茲和桃樂絲發生了什麼事,沒人知道,就連我也不清楚,某一天,他們兩個就突然消失了,直到很久以後,他們才再度出現在我的面前,對於佩蒂的造訪,對他們間的命運產生什麼樣的影響,支字不提。
現在,報喪女妖佩蒂再次站在他們面前。
我甚至可以聽見希沃茲狼牙咬緊的聲響。
報喪女妖到底是從哪個地方,接收到了什麼大宇宙的無限意志,還是從什麼地方得到的天啟,沒有人知道。
那是絕對的命運,無人得以扭轉。
報喪女妖目光溫潤的看著我們,片刻,屬於她的悅耳嗓音悠悠揚起,「伊安。」
等等,她剛剛喊誰?
伊安?哪個伊安?
那個倒楣鬼是我?我覺得有些不敢置信,活到這把年紀,就連亞里德和安德烈都沒能為我帶來永眠,這樣的我,居然會是報喪女妖這回的目標?
逗我的吧?
我有些遲疑,帶著些不敢確定的出聲詢問桃樂絲和希沃茲,「你們……剛剛有聽見佩蒂說什麼嗎?」
轉頭,我發現,方才還在我身邊,如臨大敵的兩人,早已悄悄帶著酒杯溜走,此刻正混在人群裡,對我投予既抱歉又同情的目光。
去你的友情。
我剛在心裡腹誹兩人的沒義氣,佩蒂已來到我的面前,朝我露出一個溫柔動人的微笑,「可以佔用你一點寶貴的時間嗎?」
親愛的,抱歉,我沒時間。
不好意思,我並不想和妳說話。
我心裡閃過各式各樣的拒絕辭語,表面卻是一派紳士的邀請佩蒂坐下。「當然可以。」
佩蒂也不和我客氣,乾脆入坐,讓我不由得再次怨起自己,前幾個世紀為何要和那票講究紳士精神的貴族子弟廝混,落得現在一身遺毒,想是這麼想,我心裡也很清楚,即使我扳著一張臉,叫佩蒂快滾,也改變不了什麼。
我一面意示半人馬給佩蒂端上一杯酒,一面思考佩蒂到底能給我帶來什麼消息。
佩蒂並沒有使我等太久,半人馬還沒將酒端上來,她已徐緩開口,「為您傳遞來自黑暗的問候。」
這個開場太尋常了。
我稍微思考了一下,無奈的發現,和黑暗有關,甚至可能會改變我命運,或是危及我生命的可疑怪物太多了,根本猜不出是誰。
幸虧能讓報喪女妖特地上門造訪的消息,通常不是簡短一句話就能交待的,沒多久,佩蒂便再度開口。
「您過去的棺柩已再度開啟,裡頭鋪滿了故土。」
佩蒂的話,向來隱晦又直白,她讓人可以輕易聯想到許多事,卻不能肯定到底哪件事才是關鍵,唯一可以知道的,是佩蒂講出這段話的同時原本還留在酒館內看熱鬧的怪物們,瞬間消失的無影無蹤,就彷彿今晚不曾出現過。
我看著對面坐得筆直的佩蒂,以及端著酒,此刻顯得猶豫不決的半人馬,輕笑。
真是份出人意料的驚喜。
先不說佩蒂帶來的消息到底有什麼意義,單是她提到的舊棺和故土,就相當有意思了。我來到半人馬面前,拿走那杯酒,輕輕的放在佩蒂前的桌上,「我請客。」
「噢,伊安,我知道我這麼說不太好,但是……」現在的她,不是報喪女妖,只是佩蒂,下秒,她看著那杯酒,揚起一抹有些抱歉的笑容,「我真的很慶幸,是為現在的你傳遞消息,而不是以前的你。」
「我們以前有過結?」我假裝沒有發現,半人馬躡手躡腳的離開。
「當然不是。」佩蒂像是想緩和情緒,或是其他什麼原因,拿起那杯酒抿了一口,「我只是想表達,如果換作以前的你,我應該無法活著離開。」
佩蒂的話讓我忍不住笑了出來,「妳太誇張了。」
報喪女妖是無法被消滅的,不管用怎樣的方式,怎樣的手段,哪怕將她挫骨揚灰,或是拆吃入腹,她依然會再次出現,傳達她那不知是預言,還是天啟的消息。
聽聞我的話,佩蒂一面輕笑,一面喝酒,「即此如此,被人剝皮拆骨的感覺也糟透了。」
「說的對。」我舉起酒杯,「敬夜晚。」
佩蒂會意,以她手裡的酒杯輕碰我的酒杯杯緣,「敬夜晚。」
*** *** ***
尖牙刺破肌膚,帶來的,除了疼痛,還有一絲難以言喻的顫慄,就像是施打麻啡,讓人身置夢境般的快感。
某篇以吸血鬼為題材寫的小說,內文如此寫道。
我單手支顎,看了眼在我書房內進行環境衛生打掃的安德烈,喃喃自語,「快感嗎?」
一直以來,提著水桶,拿著抹布打掃周遭環境的安德烈,總是讓我感到耐人尋味……看著捲起袖子的安德烈,還有他那隔著衣料,依舊可以感覺到底頭線條和生命力的背影,我突然感到難得的饑餓。
等我意識到時,已然開口,「安德烈。」
「嗯?」
陽光灑在轉頭看向我的安德烈身上,給了我一種彷彿我們回到過去時光的錯覺,我們曾經相處的很好,為什麼現在會變成這樣?我心裡疑問的同時,對著他伸出手,「過來。」
我想,我的尖牙應該露出來了。
安德烈放下打掃工具,朝我走來的同時,主動的解開領釦,將人類最脆弱的要害展現在我的面前。
我沒提,他沒問。
一切都是如此自然熟稔,就連我的牙齒刺入他脖子,安德烈也不曾吭過一聲,我本來不想吸食安德烈的血,直到他意外目睹我吸食人血,曝露了我吸血鬼這一身份,自那天起,我便不曾咬過他以外的人。
吸吮他的鮮血,是我認識安德烈至今,他唯一提出的要求。
哪怕後來他不知道哪根筋不對,跑去讀神學院,還成了牧師,一心想在我心臟上頭釘根木樁,只要我需要,他依然會將自己的血管曝露在我面前。
我曾經問過,為什麼想成為我的餌食?
安德烈當時沒有回答我,直到他穿著一身牧師袍,重新出現在我面前,我才從他口裡聽見答案,他說:「與其放任你到處禍害他人,不如把你限定在一定範圍裡。」
犧牲小我,完成大我的情操?
相當冠冕堂皇的理由,只是,我一點也不相信,卻也沒有深究的打算。
畢竟,一個牧師提供鮮血給吸血鬼,本身就是件受爭議的事,或者該說,這事要是曝光,安德烈惹上的麻煩,絕對比我多上不知幾倍,饒是如此,他依然義無反顧的把血管湊到我面前,我有什麼非得追根究底的理由?
人血,除了腥,還帶著一點鏽味。
將人血描寫成瓊漿玉液的傢伙,多半不曾嘗過生血的味道,除非是以這為主食的怪物,或是有特殊食物愛好癖,否則,我很難想像會有哪個人類會覺得這是種美味。
覺得饑餓受到舒解,我放開安德烈,就在這時,安德烈的聲音悠幽揚起,「伊安,你還好嗎?」
「為什麼這麼問?」我隨手從擺放在一旁的面紙盒抽出面紙,輕擦嘴唇,上頭果然沾了些安德烈的血,我將沾有血的一面對折,丟進垃圾桶,將視線移到安德烈身上。
我的吃相很好,仍是無可避免的在安德烈身上留下痕跡。
混著唾液的鮮血,在安德烈脖頸上散了開來,感覺實在有點礙眼,我忍不住抽了張面紙,替安德烈擦拭他脖頸上頭的血漬和唾液,就在這時,安德烈的嗓音再次響起,「你很久不曾吸食人血了。」
他的話語,讓我的動作為之一頓,「似乎是呢!」
我已經很久不曾進食了。
在安德烈重新以牧師之姿出現在我面前,不,也許更久之前,我們間的關係便發生了變化,從那一刻開始,我便不曾再吸過他的血。
哪怕我知道,只要我一句話,他便會將脖子湊到我面前……
直到今日,我對他提出了要求,明明我們現在的關係差到不行,他卻依然保持著固定替我整理書房的習慣,以及,為我提供鮮血。看著這樣的安德烈,看著他依然敞開的衣領,彷彿邀請我再咬上一口,我伸手替他拉了拉衣領,「不過是一時嘴饞罷了。」
我認為,自己的言論相當具有說服力。
畢竟,我可是能夠長期不吸食人血的吸血鬼。
安德烈卻只是深深的看了我一眼,把我剛替他釦好的衣領再度解開,對著我側頭,露出脖頸,「不要逞強了,伊安。」
將逞強這詞用在我身上,感覺有幾分新鮮,但,面對主動送上來的美食,我覺得,方才好不容易平復的饑餓感又冒出了一點點,我拿起方才隨手擺放在一旁的平板,滑開方才瞥過的小說片段,帶著些許不確定的詢問,「安德烈,你感到快感了嗎?」
安德烈深深的看了我一眼,那眼神讓我有些毛骨悚然。
離開書房時,安德烈衣服穿得整整齊齊,壓根半不出他前一秒在書房裡,朝我肚子打了記重拳的兇狠模樣。
就是當年被他從三樓扔下去的小偷,也沒挨過這麼重的一拳。
*** *** ***
很多人,包括怪物,都曾經問我相同的問題。
「你到底看上亞里德哪一點?」
就連身為亞里德兄長的安德烈,也曾經問過我這個問題。
那時,白天安德烈剛對我進行完一輪謀殺,晚上我便找了個理由約他喝上一杯,作為報復,我把他灌醉到保證第二天的宿醉會讓他痛不欲生,那瞬間只想重新作人的程度。
某方面來說,我覺得我挺厚道。
望了眼醉爛如泥,趴在桌上酣睡的安德烈,我不以為然的弩嘴,買酒的錢我出的,事後的環境打掃,我負責的,就連灌醉他的作程,我還陪著一起喝掉不知幾罐啤酒,最後,我還得將他安全的送回家。
世界上還有比我更加以德報怨的人嗎?
就在我開始動手清潔善後,將滿桌滿地的啤酒罐撿入垃圾袋時,身後突然傳來安德烈的聲音,「伊安。」
聞聲回頭的我,一個手抖,差點把手裡的垃圾袋給嚇掉了。
應該醉個一天一夜都爬不起床的安德烈,居然神情嚴肅,眼也不瞬的看著我,我想了下拿在手裡的啤酒空罐的重量,突然有股衝動想問他,這些年真的是去讀什麼神學院,而不是去培養酒量嗎?
當然,這些話我說不出口,因為,安德烈現在正用無比專注而認真的眼神盯著我。
再簡白一點講,我現在覺得有點害怕。
畢竟,那神情我熟悉的很,那是打從他當了牧師,我便不曾看見他表現過的本性……當年,他把人揍到牙齒噴掉,或是將小偷從三樓扔下去,用的就是這種神情。
我不怕被他從三樓丟出去,但我怕他等等會試著把我支解。
尤其是在他發現,我是蓄意將他灌醉,要讓他頭痛欲裂後……我不動聲色的確保逃生路線,一面用最輕鬆尋常的態度回應,「怎麼了嗎?」
安德烈沒有說話,只是靜靜的望著我。
我心驚膽顫的回望他,就怕他一個暴起傷人,沒想到,除了最初的喚聲,安德烈再沒任何動作,沉默的讓我覺得,自己的防備是多餘的事。
懶得跟安德烈繼續對望的我,決定繼續收拾。
就在這時,安德烈再次開口了,他說:「伊安,你喜歡亞里德什麼地方?」
這問題我聽過無數次,幾乎每個認識我跟亞里德的人都會問上這麼一次,有的甚至見一次面就問一次,但,相同的問題出自安德烈之口,感覺就是有點微妙。
我停下動作,看向安德烈。
他依然維持剛剛的姿勢,大有我不回答這問題,今晚我們誰也別想好過的意味在,我想,也許這是身為兄長,對弟弟挑選的伴侶帶有憂心的關懷吧!覺得這問題不能輕忽怠慢的我,認真的思考了下,「我想……」
安德烈挑眉,明顯在等我的下文。
「因為他很可愛吧!」這是我的肺腑之言。
論外貌,亞里德絕對稱不上令人印象深刻,或是一見傾心,說個性,小聰明之餘,他還帶了點任性跟不講道理,感情方面又是個不折不扣的兄控,我們會在一起,我自己都覺得有些不可思議,但是靜心一想,又覺得挺有道理。
這模樣的亞里德,真像我在某個世紀時曾經養過的貓。
傲嬌的有點可愛。
人類的生命短暫,甚至脆弱到禁不起一丁點的意外和傷害,在亞里德的人生裡,盡我所能的對他好,對我來說,並不是件難事。
安德烈聞言一愣,「就這樣?」
我點頭。
安德烈先是一愣,旋即笑得上氣不接下氣。
我有點擔心,他會笑到自己缺氧窒息,不過,事實很快證明,人類這種生物,不管他們是醒著,還是醉了,我永遠都摸不透。
猛然停止笑聲的安德烈,倏地起身,大步朝我走來。
就在我以為,是我剛才的回答無法令他感到滿意,他準備揍我的那瞬間,安德烈揪住我的衣領,強硬的將我拖到他面前,接著,我感到脖頸一陣劇痛……
他咬我?
他居然咬我?
這樣的認知讓我愣了幾秒,才反應過來,現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?身為人類的安德烈,居然咬我脖頸?
我該慶幸,他沒有揍我,還是該擔心下,他喝得慣生血嗎?
最後,認為此刻不宜激怒安德烈的我,輕輕推了依舊死命咬著我脖子不放的安德烈,「那個,安德烈……我們兩個裡,似乎我才是吸血……嘶……」我話還沒說完,安德烈的咬勁又重了幾分,就像是巴不得從上頭咬下一塊肉,痛得我忍不住倒抽一口氣。
如果安德烈以往讓我吸血也是這麼痛的話,他真是個漢子,能忍著不出聲。
正當我內心為安德烈的忍耐力肅然起敬時,原本死咬不放的他終於鬆口,我沒有問他,以人類的角度,吸血鬼的血液喝起來是什麼味道,或者該說,嘴上沾染鮮血卻兀自低笑的安德烈讓我問不出口。
我聽著他的笑聲,有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感覺。
好似我們間有什麼改變了,但又什麼也不曾改變。
安德烈沒再做出其他行為,他只是將頭靠在我肩上,壓根不在意,自傷口流出的鮮血會不會弄髒他的臉。
他靠著我許久,最後,低語,「伊安,你真是個混帳。」
安德烈為什麼說我是混帳,坦白說,我並沒有去思考,在這種時候,我的腦裡居然閃過不合時宜的疑問,比我還高一點的安德烈,得用多憋屈的姿勢,才能將頭靠在我肩上?這樣不會不舒服嗎?
我腦中跑過各種天馬行空的念頭,嘴巴卻自己動了起來,我說:「嗯,我是。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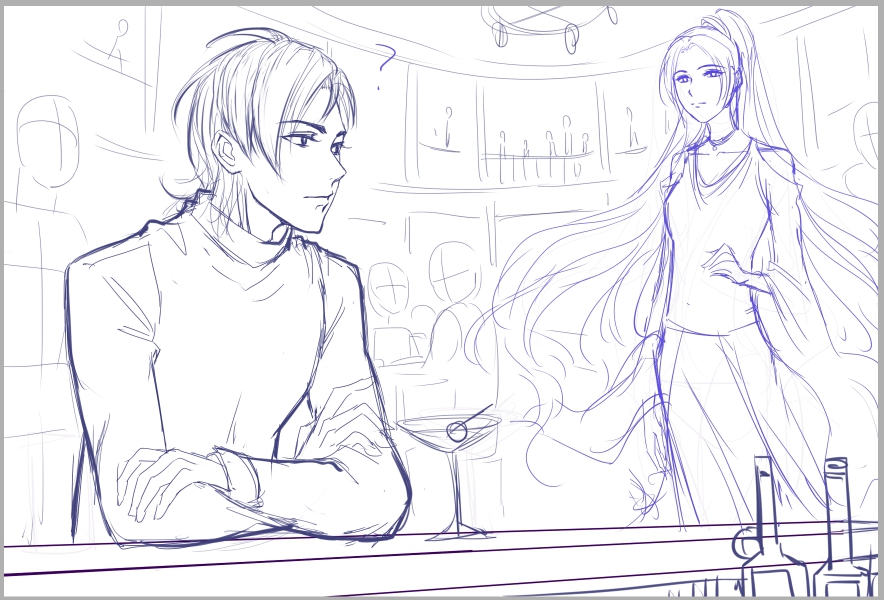

我端著酒杯,和桃樂絲與希沃茲窩在角落,觀看來來往往的怪物們。
這是一間位於偏僻處的小酒吧,外頭沒有任何的招牌告示,如果不是熟客,壓根不會想到,這個外表看似破爛,連流浪漢都不屑一顧的建築裡頭,居然藏著一間坐地明顯和外在不符,以現代建築法,絕對屬於違法擴建的古老酒館。
我第一次推開那扇門時,一度以為自己看錯了,於是我又退門口,看了看建築外部,接著才走回裡面,接受這個由怪物經營的酒館。
能把礦山大的酒館塞進不過一個房間大小的建築物裡,還沒有任何人類發現,這只能是怪物的傑作,我還來不及讚嘆這空間魔法運用的精妙,站在吧台的半人馬已走到我面前,塞了張名片給我。「新來的,享有七折優待唷!」
後來,我跟身為酒館主人的半人馬混熟後,曾感慨的表示,空間魔法真是方便,我也好想找個擅長使用空間魔法的傢伙,幫我改造一下我的住宅。
正在替我倒酒的半人馬,半是不解,半是鄙夷的看了我一眼,「空間魔法是給我們這種買不起房子的低產階級用的,你這個有房有車的怪物界勝利組,要空間魔法做什麼?」
說的好有道理,我居然無法反駁。
我端著酒杯看著酒館中來來往往的怪物們,興許是平日扮演人類實在累得夠嗆,這間酒館裡,有的只有全然的怪物,對,就是那種毫不掩飾,該纏著繃帶就纏著繃帶,該渾身毛皮就渾身毛皮,怎麼隨意怎麼來的怪物們。
堅守人類世界守則,堅持扮作人類的怪物,在這只會被罵作是衣冠禽獸。
如果以人類的角度來看怪物間的情誼,大概會是薄情炎涼,諸如此類的評價。
我們不太可能因為一時想念,就繞過半個地球去探望對方,雖然會這麼做的怪物,本質上還是存在的,但是終究是少部份,畢竟,我們的壽命與時間和人類不同。
幾十年,對人類來說,興許是一輩子的時光,對我們而言,不過是頓下午茶,甚至是眨眼間的事,話雖如此,偶爾我們還是會在這間酒吧碰頭。
畢竟有些事,不是知根知底的人,實在難以理解。
活了幾百年的傢伙,一天起床,突然覺得生活枯燥乏味,想找個人發發牢騷,或是那天心情不好,想把什麼人的骨頭給拆下來,再重新組裝,最好不用負起任何法律責任,怪物是你最好的選擇。
有個不知死活的傢伙,跑去詢問前面那桌的棕精靈,最近怎麼沒見他們潛入別人家裡,幫忙人類作家事?
早已喝得滿臉通紅的棕精靈,當下就砸了酒杯、掀翻桌子,揪著對方一頓狂打。「現代人家裡都有掃地機器人,還要我們做什麼!」
又是一個因為科技發達而失業的不幸故事。
棕精靈和人幹架的場面不常見,整個酒館的人都興味勃勃的看著他們揪著對方衣領,又是揮拳,又是頭鎚,身為酒館主人的半人馬,甚至抓準商機,當下就開了賭局。
我看了下賠率,思考是否該去玩一把?
叮嚀。
安裝在門扉上的風鈴發出清脆聲響,吸引了部份人的注意。
一開始是率先注意到新訪客的人,接著,察覺到這份異常的人好奇的往入口一看,接著,原本喧嘩的酒館,瞬間靜了下來。
就連打到眼紅的棕精靈也停下動作,眼也不瞬的盯著女妖。
女妖穿著一襲雪白長裙,那襲衣袍,與其說是紗,更像白霧,又像是暮夜月光,在空中輕輕飄蕩。
就是這麼一位女妖,對整個酒館施加了一項名為沉默的魔法。
每個人都靜靜的望著她。
女妖在怪物界極其有名。
如果要用人類來舉例,她大概就像是埃及的克麗奧佩脫拉,中國的蘇妲己,或是近代的奧黛麗赫本與瑪莉蓮夢露。
她甚至是我所見過的女妖中,最美的一位。
不單是我,在場所有怪物都如此認同,如果換作平常時候,不管是人類,還是怪物,都很樂意請她喝上一杯,但是,今天,沒有人上前向她搭訕。
曾經有人問我,覺得哪個怪物最讓人類討厭?
我沒法回答這問題,畢竟人類的喜好太難理解,哪怕是最可愛的怪物,人類中也有人會對其抱持強烈的痛恨感,但是,如果將問題改成,怪物界中,最讓怪物排斥的怪物是誰?我相信,這個答案只會是佩蒂。
佩蒂雖然是公認的第一美女,個性也相當溫和好相處,但,她穿上那襲長袍時,沒有任何一個怪物會想見到她。
因為佩蒂是個報喪女妖。
一個專門帶來壞消息的報喪女妖,最糟的是,佩蒂帶來的,不只是訃聞,有時她會帶來一些令怪物們的生活產生劇烈改變的消息。
準確度還是令人髮指的百分百。
因為佩蒂的登門造訪而改變一生的怪物難以算清,要命的是,不管對方躲在哪裡,只要還有一口氣在,哪怕躲在荒涼無人的深山叢林,或是深埋地底數丈,佩蒂總能找到他們。
比人類的尋人節目還高效率。
許久以前,曾經有人不知死活的對佩蒂開玩笑,讓她去當個尋人偵探,絕對賺錢,結果,佩蒂揚起一抹有些為難的淺淡笑容,「嗯,我想你們對我有點誤會,我只能找到必須通報消息的對象。」
佩蒂那時說的雲淡風輕,聽的人卻是頭皮發麻。
話題扯遠了。
此刻將報喪女妖那身行頭穿在身上的佩蒂,目光在酒館裡來回巡視,就是這麼一個簡單的動作,讓酒館內本就沉默的氣氛更加壓抑。
誰是這回的倒楣鬼?
我腦裡剛浮現這個疑問,佩蒂的目光已落在我們這桌。
幾乎是在那一瞬間,在我們前頭的怪物們,不管是站或坐,全部跑得老遠,畫面之壯觀,不亞於摩西分海,雖然,我根本沒見過一個叫摩西的人類,也不曾看過他怎麼劈開紅海,劃出一條道路。
最混帳的是,他們撤開時,順道將阻隔在佩蒂和我們之間的桌椅都一塊搬走了。
這也讓道的太過份了點。
我還來不及說些什麼,便清楚感覺到希沃茲全身的肌肉都繃緊了,就連桃樂絲也死死捏著酒杯,報喪女妖的威力,連向來無所畏懼的桃樂絲也不敢忽視。
許久以前,佩蒂曾以報喪女妖的身份找上他們兩人,希沃茲和桃樂絲發生了什麼事,沒人知道,就連我也不清楚,某一天,他們兩個就突然消失了,直到很久以後,他們才再度出現在我的面前,對於佩蒂的造訪,對他們間的命運產生什麼樣的影響,支字不提。
現在,報喪女妖佩蒂再次站在他們面前。
我甚至可以聽見希沃茲狼牙咬緊的聲響。
報喪女妖到底是從哪個地方,接收到了什麼大宇宙的無限意志,還是從什麼地方得到的天啟,沒有人知道。
那是絕對的命運,無人得以扭轉。
報喪女妖目光溫潤的看著我們,片刻,屬於她的悅耳嗓音悠悠揚起,「伊安。」
等等,她剛剛喊誰?
伊安?哪個伊安?
那個倒楣鬼是我?我覺得有些不敢置信,活到這把年紀,就連亞里德和安德烈都沒能為我帶來永眠,這樣的我,居然會是報喪女妖這回的目標?
逗我的吧?
我有些遲疑,帶著些不敢確定的出聲詢問桃樂絲和希沃茲,「你們……剛剛有聽見佩蒂說什麼嗎?」
轉頭,我發現,方才還在我身邊,如臨大敵的兩人,早已悄悄帶著酒杯溜走,此刻正混在人群裡,對我投予既抱歉又同情的目光。
去你的友情。
我剛在心裡腹誹兩人的沒義氣,佩蒂已來到我的面前,朝我露出一個溫柔動人的微笑,「可以佔用你一點寶貴的時間嗎?」
親愛的,抱歉,我沒時間。
不好意思,我並不想和妳說話。
我心裡閃過各式各樣的拒絕辭語,表面卻是一派紳士的邀請佩蒂坐下。「當然可以。」
佩蒂也不和我客氣,乾脆入坐,讓我不由得再次怨起自己,前幾個世紀為何要和那票講究紳士精神的貴族子弟廝混,落得現在一身遺毒,想是這麼想,我心裡也很清楚,即使我扳著一張臉,叫佩蒂快滾,也改變不了什麼。
我一面意示半人馬給佩蒂端上一杯酒,一面思考佩蒂到底能給我帶來什麼消息。
佩蒂並沒有使我等太久,半人馬還沒將酒端上來,她已徐緩開口,「為您傳遞來自黑暗的問候。」
這個開場太尋常了。
我稍微思考了一下,無奈的發現,和黑暗有關,甚至可能會改變我命運,或是危及我生命的可疑怪物太多了,根本猜不出是誰。
幸虧能讓報喪女妖特地上門造訪的消息,通常不是簡短一句話就能交待的,沒多久,佩蒂便再度開口。
「您過去的棺柩已再度開啟,裡頭鋪滿了故土。」
佩蒂的話,向來隱晦又直白,她讓人可以輕易聯想到許多事,卻不能肯定到底哪件事才是關鍵,唯一可以知道的,是佩蒂講出這段話的同時原本還留在酒館內看熱鬧的怪物們,瞬間消失的無影無蹤,就彷彿今晚不曾出現過。
我看著對面坐得筆直的佩蒂,以及端著酒,此刻顯得猶豫不決的半人馬,輕笑。
真是份出人意料的驚喜。
先不說佩蒂帶來的消息到底有什麼意義,單是她提到的舊棺和故土,就相當有意思了。我來到半人馬面前,拿走那杯酒,輕輕的放在佩蒂前的桌上,「我請客。」
「噢,伊安,我知道我這麼說不太好,但是……」現在的她,不是報喪女妖,只是佩蒂,下秒,她看著那杯酒,揚起一抹有些抱歉的笑容,「我真的很慶幸,是為現在的你傳遞消息,而不是以前的你。」
「我們以前有過結?」我假裝沒有發現,半人馬躡手躡腳的離開。
「當然不是。」佩蒂像是想緩和情緒,或是其他什麼原因,拿起那杯酒抿了一口,「我只是想表達,如果換作以前的你,我應該無法活著離開。」
佩蒂的話讓我忍不住笑了出來,「妳太誇張了。」
報喪女妖是無法被消滅的,不管用怎樣的方式,怎樣的手段,哪怕將她挫骨揚灰,或是拆吃入腹,她依然會再次出現,傳達她那不知是預言,還是天啟的消息。
聽聞我的話,佩蒂一面輕笑,一面喝酒,「即此如此,被人剝皮拆骨的感覺也糟透了。」
「說的對。」我舉起酒杯,「敬夜晚。」
佩蒂會意,以她手裡的酒杯輕碰我的酒杯杯緣,「敬夜晚。」
*** *** ***
尖牙刺破肌膚,帶來的,除了疼痛,還有一絲難以言喻的顫慄,就像是施打麻啡,讓人身置夢境般的快感。
某篇以吸血鬼為題材寫的小說,內文如此寫道。
我單手支顎,看了眼在我書房內進行環境衛生打掃的安德烈,喃喃自語,「快感嗎?」
一直以來,提著水桶,拿著抹布打掃周遭環境的安德烈,總是讓我感到耐人尋味……看著捲起袖子的安德烈,還有他那隔著衣料,依舊可以感覺到底頭線條和生命力的背影,我突然感到難得的饑餓。
等我意識到時,已然開口,「安德烈。」
「嗯?」
陽光灑在轉頭看向我的安德烈身上,給了我一種彷彿我們回到過去時光的錯覺,我們曾經相處的很好,為什麼現在會變成這樣?我心裡疑問的同時,對著他伸出手,「過來。」
我想,我的尖牙應該露出來了。
安德烈放下打掃工具,朝我走來的同時,主動的解開領釦,將人類最脆弱的要害展現在我的面前。
我沒提,他沒問。
一切都是如此自然熟稔,就連我的牙齒刺入他脖子,安德烈也不曾吭過一聲,我本來不想吸食安德烈的血,直到他意外目睹我吸食人血,曝露了我吸血鬼這一身份,自那天起,我便不曾咬過他以外的人。
吸吮他的鮮血,是我認識安德烈至今,他唯一提出的要求。
哪怕後來他不知道哪根筋不對,跑去讀神學院,還成了牧師,一心想在我心臟上頭釘根木樁,只要我需要,他依然會將自己的血管曝露在我面前。
我曾經問過,為什麼想成為我的餌食?
安德烈當時沒有回答我,直到他穿著一身牧師袍,重新出現在我面前,我才從他口裡聽見答案,他說:「與其放任你到處禍害他人,不如把你限定在一定範圍裡。」
犧牲小我,完成大我的情操?
相當冠冕堂皇的理由,只是,我一點也不相信,卻也沒有深究的打算。
畢竟,一個牧師提供鮮血給吸血鬼,本身就是件受爭議的事,或者該說,這事要是曝光,安德烈惹上的麻煩,絕對比我多上不知幾倍,饒是如此,他依然義無反顧的把血管湊到我面前,我有什麼非得追根究底的理由?
人血,除了腥,還帶著一點鏽味。
將人血描寫成瓊漿玉液的傢伙,多半不曾嘗過生血的味道,除非是以這為主食的怪物,或是有特殊食物愛好癖,否則,我很難想像會有哪個人類會覺得這是種美味。
覺得饑餓受到舒解,我放開安德烈,就在這時,安德烈的聲音悠幽揚起,「伊安,你還好嗎?」
「為什麼這麼問?」我隨手從擺放在一旁的面紙盒抽出面紙,輕擦嘴唇,上頭果然沾了些安德烈的血,我將沾有血的一面對折,丟進垃圾桶,將視線移到安德烈身上。
我的吃相很好,仍是無可避免的在安德烈身上留下痕跡。
混著唾液的鮮血,在安德烈脖頸上散了開來,感覺實在有點礙眼,我忍不住抽了張面紙,替安德烈擦拭他脖頸上頭的血漬和唾液,就在這時,安德烈的嗓音再次響起,「你很久不曾吸食人血了。」
他的話語,讓我的動作為之一頓,「似乎是呢!」
我已經很久不曾進食了。
在安德烈重新以牧師之姿出現在我面前,不,也許更久之前,我們間的關係便發生了變化,從那一刻開始,我便不曾再吸過他的血。
哪怕我知道,只要我一句話,他便會將脖子湊到我面前……
直到今日,我對他提出了要求,明明我們現在的關係差到不行,他卻依然保持著固定替我整理書房的習慣,以及,為我提供鮮血。看著這樣的安德烈,看著他依然敞開的衣領,彷彿邀請我再咬上一口,我伸手替他拉了拉衣領,「不過是一時嘴饞罷了。」
我認為,自己的言論相當具有說服力。
畢竟,我可是能夠長期不吸食人血的吸血鬼。
安德烈卻只是深深的看了我一眼,把我剛替他釦好的衣領再度解開,對著我側頭,露出脖頸,「不要逞強了,伊安。」
將逞強這詞用在我身上,感覺有幾分新鮮,但,面對主動送上來的美食,我覺得,方才好不容易平復的饑餓感又冒出了一點點,我拿起方才隨手擺放在一旁的平板,滑開方才瞥過的小說片段,帶著些許不確定的詢問,「安德烈,你感到快感了嗎?」
安德烈深深的看了我一眼,那眼神讓我有些毛骨悚然。
離開書房時,安德烈衣服穿得整整齊齊,壓根半不出他前一秒在書房裡,朝我肚子打了記重拳的兇狠模樣。
就是當年被他從三樓扔下去的小偷,也沒挨過這麼重的一拳。
*** *** ***
很多人,包括怪物,都曾經問我相同的問題。
「你到底看上亞里德哪一點?」
就連身為亞里德兄長的安德烈,也曾經問過我這個問題。
那時,白天安德烈剛對我進行完一輪謀殺,晚上我便找了個理由約他喝上一杯,作為報復,我把他灌醉到保證第二天的宿醉會讓他痛不欲生,那瞬間只想重新作人的程度。
某方面來說,我覺得我挺厚道。
望了眼醉爛如泥,趴在桌上酣睡的安德烈,我不以為然的弩嘴,買酒的錢我出的,事後的環境打掃,我負責的,就連灌醉他的作程,我還陪著一起喝掉不知幾罐啤酒,最後,我還得將他安全的送回家。
世界上還有比我更加以德報怨的人嗎?
就在我開始動手清潔善後,將滿桌滿地的啤酒罐撿入垃圾袋時,身後突然傳來安德烈的聲音,「伊安。」
聞聲回頭的我,一個手抖,差點把手裡的垃圾袋給嚇掉了。
應該醉個一天一夜都爬不起床的安德烈,居然神情嚴肅,眼也不瞬的看著我,我想了下拿在手裡的啤酒空罐的重量,突然有股衝動想問他,這些年真的是去讀什麼神學院,而不是去培養酒量嗎?
當然,這些話我說不出口,因為,安德烈現在正用無比專注而認真的眼神盯著我。
再簡白一點講,我現在覺得有點害怕。
畢竟,那神情我熟悉的很,那是打從他當了牧師,我便不曾看見他表現過的本性……當年,他把人揍到牙齒噴掉,或是將小偷從三樓扔下去,用的就是這種神情。
我不怕被他從三樓丟出去,但我怕他等等會試著把我支解。
尤其是在他發現,我是蓄意將他灌醉,要讓他頭痛欲裂後……我不動聲色的確保逃生路線,一面用最輕鬆尋常的態度回應,「怎麼了嗎?」
安德烈沒有說話,只是靜靜的望著我。
我心驚膽顫的回望他,就怕他一個暴起傷人,沒想到,除了最初的喚聲,安德烈再沒任何動作,沉默的讓我覺得,自己的防備是多餘的事。
懶得跟安德烈繼續對望的我,決定繼續收拾。
就在這時,安德烈再次開口了,他說:「伊安,你喜歡亞里德什麼地方?」
這問題我聽過無數次,幾乎每個認識我跟亞里德的人都會問上這麼一次,有的甚至見一次面就問一次,但,相同的問題出自安德烈之口,感覺就是有點微妙。
我停下動作,看向安德烈。
他依然維持剛剛的姿勢,大有我不回答這問題,今晚我們誰也別想好過的意味在,我想,也許這是身為兄長,對弟弟挑選的伴侶帶有憂心的關懷吧!覺得這問題不能輕忽怠慢的我,認真的思考了下,「我想……」
安德烈挑眉,明顯在等我的下文。
「因為他很可愛吧!」這是我的肺腑之言。
論外貌,亞里德絕對稱不上令人印象深刻,或是一見傾心,說個性,小聰明之餘,他還帶了點任性跟不講道理,感情方面又是個不折不扣的兄控,我們會在一起,我自己都覺得有些不可思議,但是靜心一想,又覺得挺有道理。
這模樣的亞里德,真像我在某個世紀時曾經養過的貓。
傲嬌的有點可愛。
人類的生命短暫,甚至脆弱到禁不起一丁點的意外和傷害,在亞里德的人生裡,盡我所能的對他好,對我來說,並不是件難事。
安德烈聞言一愣,「就這樣?」
我點頭。
安德烈先是一愣,旋即笑得上氣不接下氣。
我有點擔心,他會笑到自己缺氧窒息,不過,事實很快證明,人類這種生物,不管他們是醒著,還是醉了,我永遠都摸不透。
猛然停止笑聲的安德烈,倏地起身,大步朝我走來。
就在我以為,是我剛才的回答無法令他感到滿意,他準備揍我的那瞬間,安德烈揪住我的衣領,強硬的將我拖到他面前,接著,我感到脖頸一陣劇痛……
他咬我?
他居然咬我?
這樣的認知讓我愣了幾秒,才反應過來,現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?身為人類的安德烈,居然咬我脖頸?
我該慶幸,他沒有揍我,還是該擔心下,他喝得慣生血嗎?
最後,認為此刻不宜激怒安德烈的我,輕輕推了依舊死命咬著我脖子不放的安德烈,「那個,安德烈……我們兩個裡,似乎我才是吸血……嘶……」我話還沒說完,安德烈的咬勁又重了幾分,就像是巴不得從上頭咬下一塊肉,痛得我忍不住倒抽一口氣。
如果安德烈以往讓我吸血也是這麼痛的話,他真是個漢子,能忍著不出聲。
正當我內心為安德烈的忍耐力肅然起敬時,原本死咬不放的他終於鬆口,我沒有問他,以人類的角度,吸血鬼的血液喝起來是什麼味道,或者該說,嘴上沾染鮮血卻兀自低笑的安德烈讓我問不出口。
我聽著他的笑聲,有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感覺。
好似我們間有什麼改變了,但又什麼也不曾改變。
安德烈沒再做出其他行為,他只是將頭靠在我肩上,壓根不在意,自傷口流出的鮮血會不會弄髒他的臉。
他靠著我許久,最後,低語,「伊安,你真是個混帳。」
安德烈為什麼說我是混帳,坦白說,我並沒有去思考,在這種時候,我的腦裡居然閃過不合時宜的疑問,比我還高一點的安德烈,得用多憋屈的姿勢,才能將頭靠在我肩上?這樣不會不舒服嗎?
我腦中跑過各種天馬行空的念頭,嘴巴卻自己動了起來,我說:「嗯,我是。」